“布草”是我們對(duì)社會(huì)服務(wù)業(yè)所使用公用紡織品一類用品的統(tǒng)稱���。不過這個(gè)稱呼被全行業(yè)共同接受和認(rèn)知僅是近幾十年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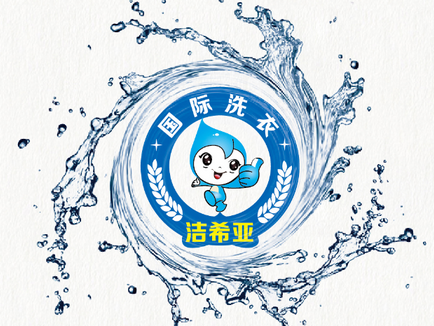
過去�,這類公用紡織品衣物在各地的稱呼各不相同,有的稱作“白活”���,有的稱作“行(讀hang)活”�����,有的則稱作臥具�,還有的稱作團(tuán)體活等等��。其實(shí)“布草”一詞約有百十來年�����,最早源自港澳地區(qū)用于稱呼公用紡織品。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外合資酒店的逐漸開辦才傳入內(nèi)地����,最后形成了洗染行業(yè)的共識(shí)。
早期國(guó)內(nèi)旅店業(yè)使用的臥具大多都自己洗�����,具有一定檔次的賓館酒店才開設(shè)有像樣的洗衣房。但也有一些略具規(guī)模的旅店會(huì)把這些臥具委托給社會(huì)上的洗衣坊洗。后來�����,鐵路客運(yùn)的臥鋪臥具也進(jìn)入了這個(gè)系列�����,于是逐漸就出現(xiàn)了專門為旅店���、臥鋪車廂和醫(yī)院服務(wù)“洗白活”�。主要是洗滌床單�����、褥單����、被單����、枕巾、枕套等等。那時(shí)還沒有被罩一類的東西���,被子和褥子都要拆開洗滌,然后重新縫制。由于洗白活的品種雖然相對(duì)簡(jiǎn)單一些但批量相對(duì)較大,于是漸漸地就形成了潔希亞的專門工藝。并且形成了一套專門的操作方法和創(chuàng)制了一套相應(yīng)的專業(yè)工具與設(shè)施。
打蒸鍋
不論洗什么樣的衣服必然要使用一些熱水�,洗白活就更需要使采用熱水���。拉風(fēng)箱燒熱水就成了小徒弟的專職。不過這還不是最艱苦的活兒��,整天去井里打水挑水才是新進(jìn)門徒弟的差事����。后來有條件的洗衣店安裝了壓水機(jī),徒弟基本上不必挑水了����,改成了整天壓水��。
人所共知,洗白活需要的熱水量很大,人工燒熱水根本就供不上使用。怎樣才能把白活洗得又白又干凈呢,于是“打蒸鍋”應(yīng)運(yùn)而生�����。
洗衣坊用于打蒸鍋的大鐵鍋很大�,直徑有一米多。上面安放著一個(gè)沒有底的大木桶圈���,足有一米多高。大鐵鍋里燒著配好的肥皂堿水��,鍋里還安放著一個(gè)木制的蓖子��。白活取回以后先把它們理順�����,每?jī)扇齻€(gè)床單(或是被里等)一組。在已經(jīng)準(zhǔn)備好的熱肥皂堿水中浸透然后擰成一把���,大約一尺多長(zhǎng)三四寸粗細(xì)的樣子。這個(gè)過程叫做“打把兒”�。把打好的把兒像壘磚一樣緊貼著木桶內(nèi)壁整齊地碼放在鍋里的蓖子上����。正中間留了一個(gè)直通上下約有碗口粗的通道���。待把木桶內(nèi)的空間碼放滿了以后����,上面蓋上干凈的白單子和棉被����。這時(shí)徒弟開始緊拉風(fēng)箱燒大火�,這個(gè)打蒸鍋的初步過程就算是告成了��。
大火燒上將近一個(gè)小時(shí)���,木桶里的所有單子都已經(jīng)蒸透���,同時(shí)所有的單子也被滾燙的肥皂堿水再一次浸透����。這時(shí)��,高高的木捅頂上不但胃著濃重的蒸汽同時(shí)還涌出了密密麻麻的肥皂沫�����,蒸鍋就可以打開出鍋了。這樣的一組蒸鍋可以裝上二三百條單子����,出鍋以后取出單子就要進(jìn)行手工搓洗的過程�����。
搓大桶
過去洗衣坊所有的活兒完全都是手工操作��,最為關(guān)鍵的的白活洗滌過程自然也不例外�����,經(jīng)過打蒸鍋以后的單子已經(jīng)熱的燙手,這時(shí)正是手工搓洗的最好時(shí)機(jī)����。搓洗時(shí)使用的也是一個(gè)大木桶��,將近六七十厘米粗細(xì)也有一米來高,里面放著一個(gè)碩大的木制搓板�����。那搓板有一尺多寬���,一米多長(zhǎng)���,四五厘米厚��,搓板的溝槽也有半寸多深��,足有幾十斤重。由于常年浸泡在水中,那搓板從來不會(huì)漂浮起來,乖乖的呆在木桶里。操作者就在這種木桶中通過大搓板搓洗單子。而投水漂洗的過程亦如搓洗時(shí)一樣,也是使用同樣的木桶和搓板��。但每個(gè)投水的大木桶里都有一根水管子不斷地往桶里注入清水��,同時(shí)把那些已經(jīng)渾濁的水慢慢排出去���,這稱作“流通水”�。
為了提高勞動(dòng)效率�����,搓洗和每次投水漂洗采取一人一個(gè)崗位的流水操作方式。由一個(gè)人負(fù)責(zé)搓洗,三個(gè)人負(fù)責(zé)投水漂洗�。這種手工搓洗和漂洗的過程就叫做“搓大桶”���。因?yàn)椴僮鲌?chǎng)地到處都是水���,所以干活的人各個(gè)都穿著長(zhǎng)筒膠靴胸前戴著膠布圍裙�。一天下來�,操作者個(gè)個(gè)腰酸背痛疲憊不堪。冬季,搓洗的人雖然守著熱單子不會(huì)受凍,由于溫度太高當(dāng)然不免汗流淡背��。而從始至終都是使用冷水投水漂洗的人則是冷徹筋骨��。到了夏季�����,投水漂洗的人倒是涼快了一些�����,而負(fù)責(zé)搓洗的人卻是酷熱難當(dāng)大汗淋漓。甚至什么都不穿整日裸露著全身干活。
牛角樁和絞杠
搓洗和投水漂洗以后�����,各種單子己經(jīng)洗滌完畢非常干凈�。接著就是如何把單子上面的水盡可能的絞擰干凈,使其能夠很快地晾干。
投水漂洗的最后一個(gè)人負(fù)責(zé)把單子重新打把兒��,為下一步絞干水分做好準(zhǔn)備����。由于那時(shí)并沒有脫水機(jī),絞干水分要靠一個(gè)“牛角樁”和“絞杠”來完成�����。
牛角樁大多由廢舊的房梁改制而成��。大約有二三十厘米粗細(xì),足有兩三米長(zhǎng)����。下面的一半垂直埋在地下���,另一半約有一米多露出地面之上����,在上部橫穿著一根幾厘米粗的橫杠�。活像一個(gè)牛頭的兩只角����,因此叫做“牛角樁”���。立柱和橫杠都是硬雜木制成的����,而且經(jīng)過仔細(xì)地打磨����,表面非常光滑。干活時(shí)����,還有一根大小很像搟面杖的絞杠�����,負(fù)責(zé)絞水的人把打好打把兒的單子繞在牛角裝橫杠和絞杠之間用力向后面拉緊���,同時(shí)旋轉(zhuǎn)著擰絞單子��,于是大量的水分就被擰絞下來了��。
經(jīng)過絞擰的單子和如今經(jīng)過脫水機(jī)甩干的單子不相上下,這時(shí)就可以上架子晾干了�。有的單子使用的時(shí)間較長(zhǎng)一些�����,經(jīng)過這樣一絞竟能夠全然破碎?����?梢姴僮髋=菢督g杠的人真是練就了一身好功夫���。為此�����,擰絞那些較為陳舊單子的時(shí)候他們一定要悠著勁兒����。
洗衣坊的晾活架子

所洗的各種單子經(jīng)過絞干以后就要去室外晾干,洗衣坊的晾活架子非常有特色�����,每組晾活架子由三根立桿組成���,牢牢地栽在地上���。中間一根是主桿兩側(cè)是副桿���,最早主桿和副桿都用的是衫篙���,后來改成了十厘米左右的鋼管���。三根桿子至少有五六米高����,甚至有的更高�,它們排列成一行大約相距有十來米。主桿的頂端固定著滑輪,用它好把晾衣繩拉起來�����。晾衣繩的中間用一根繩子拴住�����,向上正好穿過主桿上面的滑輪�����,以便通過滑輪拉到高處,晾衣繩的兩端各栓著一個(gè)鐵環(huán)鐵環(huán)套在副桿上��,這兩端的鐵環(huán)可以使晾衣繩沿著副桿上下滑動(dòng)���。當(dāng)晾衣繩夾滿了單子時(shí)就可以把晾衣繩提拉到高處了���。
這種晾活架子大多由兩三組或更多的組成一個(gè)方陣一方面能夠擴(kuò)大晾活量�,一方面便于把晾活架子之間相互支撐固定����。
操作時(shí)需要三個(gè)人相互配合,一個(gè)人負(fù)責(zé)把拉繩用力拉到桿子的高處���,另外兩個(gè)人各使用一根帶有叉子的大竹竿推動(dòng)副桿上的鐵環(huán)逐漸升高。晾滿了繩的濕單子足有二三百斤重��,雖然三個(gè)人同時(shí)操作一起往上連推帶拉����,仍然需要棒小伙才能干的了。晾衣繩拉到高處以后被牢牢地拴住����,固定在主桿的下面���,這一根就算是完成了�����。每組晾活架子都有三根繩子,分成高、中、低三層��。這樣一組晾活架子可以晾曬好幾百個(gè)單子��。
最值得稱道的是晾衣繩的結(jié)構(gòu)�。晾衣繩一般使用質(zhì)地非常好猶如手指粗細(xì)的棉線繩。為了防止繩子把洗好的單子污染,新買的繩子在使用前一定要經(jīng)過肥皂堿水的煮練,直至沒有任何漿性才能上桿��。不然��,晾干的單子上就可能留下黃色的印子�,那是絕對(duì)不可以的�。晾衣繩采用兩股相互絞在一起�,但彼此并不是絞的很緊,看起來松松垮垮的�。不過�,這個(gè)松緊程度卻非常有講究����。那兩股繩子的縫隙正是晾曬單子的夾緊扣。而每個(gè)單子只需要夾住兩三個(gè)角��。當(dāng)所有繩子的縫隙都夾滿了單子以后����,那晾衣繩正好變得極其緊實(shí),所有的單子都被繩子牢牢地夾住�。晾衣繩掛在五六米的高空�����,只要不超過八級(jí)大風(fēng)所有的單子都不會(huì)被刮掉下來。盡管北方春天風(fēng)干物燥大風(fēng)頻顧�,洗衣坊高高的晾活架子上掛滿了啪啪作響的白單子����,卻能無一脫落可謂一絕���。
“打蒸鍋”隨著熱水鍋爐和蒸汽鍋爐的使用�,在20世紀(jì)50年代以后就逐漸地消失了?��!按甏笸啊币苍趪?guó)內(nèi)能夠生產(chǎn)半自動(dòng)工業(yè)洗衣機(jī)的五六十年代被取代。就在同一時(shí)期���,“牛角樁”和“絞杠”也在那時(shí)候被脫水機(jī)所取代。全國(guó)的洗染業(yè)在五六十年代前后逐漸完成了生產(chǎn)機(jī)械化的技術(shù)改造和進(jìn)步��。完全靠手工生產(chǎn)的狀況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而布草洗滌能夠使用燙平機(jī)、烘干機(jī)進(jìn)行軋平和干燥則相對(duì)要晚一些���。所以���,晾活架子直到20世紀(jì)70年代才徹底被取代而消失����。